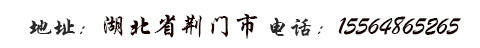乡村记事养蚕
|
乡村记事-养蚕 养蚕缫丝是极古老的农事,相传*帝的妻子嫘祖发明:从诗经唐诗宋词的一路走来,近五千年的历史,采桑的罗敷女红颜白发多少个轮回,陌上桑采桑子萦绕在诗人游子的羁旅生涯中,巧手的织女们使用各种繁复的手法织成纺、绉、缎、绫、纱、罗、绒、锦、绡、葛、绨、绢、绸、呢,更有种种绣工锦上添花,苏绣蜀绣湘绣不胜枚举……中华文明,丝绸,是其中最柔软而瑰丽的篇章。 然后,让我们来到这广袤大地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落,皖南一个小小的乡村。抛去那些现代社会的附着物,乡村的农事,其实和几千年前没有巨大的差别,至少在养蚕的步骤方法上,与度娘对嫘祖“种桑养蚕之法,抽丝编绢之术”的介绍十分相类----文化的传承,庙堂朝野,源远流长。 蚕喜暖好湿,总要到四月底五月初,暮春桃李芳菲已尽,油菜花一片明*,母亲会拿回一两张纸,上面密密麻麻附着黑色的蚕卵----所以,养蚕的计量单位是“养了几张纸”。放在竹匾中,似乎是要盖上一层布,不知是避光还是保暖。四五天之后,掀开一看,黑色的蚕卵已经透明,竹匾上布上爬满了蚂蚁一样的幼蚕。母亲拿这一根鸡毛小心翼翼地将布上的幼蚕扫下来,洒一层切得细细的嫩桑叶,蚕事正式开始。 桑树发芽长叶,和着春蚕成长的脚步,点点嫩芽伴随幼蚕经过了最初的四五天,到了一眠,幼蚕 次蜕皮,不再是小黑蚂蚁了,十来毫米长,蠕动着的小虫。一个竹匾不够了,分到几个竹匾中,食量自然也大了起来,几片桑叶不够,母亲给个小竹篮,此时采桑叶是很轻省的活计,半大丫头小子也做得,只是不懂如何间隔着挑叶,紧着一棵桑树采,母亲看到是要呵斥的。桑叶采回,要细细擦干,尤其是蚕小的时候,带水的桑叶吃了,很容易生病,一死一大片的,一匾一匾地倒,母亲心疼得紧。 养蚕的过程,采桑上叶除沙,随着蚕的长大,活计越来越重了。一眠二眠三眠四眠,每隔五六天,蚕宝宝会不吃不喝停顿一两天蜕一次皮,越来越圆滚滚的,颜色也从黑到青绿再到青白 能看到表皮之下包裹的莹白的丝胶。三眠之后,吃得又快又多,桑叶铺上去,沙沙细雨声,一二十个大竹匾, 一个上完叶, 个已经吃完。大人吃饭都没时间,小竹篮哪够,挑一对大竹篓。桑叶不能掰下来,会影响后续发芽,食指拇指掐断叶柄,几天下来,手指头都是青肿的。要是一连雨天,也不能不出去采桑叶啊,一根桑树枝弯下来,雨水流进衣袖领口,挑着的那担桑叶,水淋淋的足有几倍重量,路上的泥泞顾不得,蚕宝宝饿着肚子等着呢。 小学生经常为完成老师布置的特殊作业,养几条蚕观察其生长过程,放在小盒子里面,除沙时不过把蚕拿起来放到另外一个盒子里,倒掉原来盒子里的蚕沙(蚕宝宝的排泄物)即可。农家养蚕,这样一条一条地捉,蚕不饿死,自己也该饿死了。一般竹匾上会放一层网,蚕在上面,蚕沙落在下面,除砂时,两个人抓住四个角连网带蚕抬到一个空匾中,剩下的蚕沙收在一起,沃在桑树地下,是极好的有机肥料。 春蚕开始虽已四五月份,有时还有些料峭的春寒,幼蚕喜温喜湿,记得母亲会将竹匾放在小房间里,围着塑料薄膜,还要放几个火熥。邻居左右,也都互通着有无,谁家好本事,养了三张纸;谁家比较暖和,蚕都二眠了;遇到 桑叶不够,招呼一声,自己到邻居桑林里采,亦属平常。四五十天的时间,家里家外,农妇口头谈的都是蚕事。大眠过后,蚕宝宝不再吃叶,排出体内绿色蚕沙,通体透明,该上山了。所谓的“山”,是稻草折成的一个个架子,有一个个支撑点,便于吐丝结茧。将熟蚕一条条放到上去,六七天后,一个一个洁白的蚕茧藏在稻草山中。最喜欢和父母一起摘茧了:收获的喜悦,一家人聊着家常,一篮茧好轻,丝自然的银白,缫出丝来,素色的也极美的,不知今年茧价如何?县城有缫丝厂丝绸厂,门店卖的丝巾真漂亮----也就看看,庄户人家,戴那个不保暖不说,拖拖拉拉的,怎么干活? 桑树除却桑叶饲蚕,对小孩子来说,更感兴趣的是其副产品桑葚。小山村里没什么果树,也无闲钱到县城买个苹果香蕉,桑葚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应该是夏天了,记得学校中午要午睡,几个小子丫头偷偷出去采桑葚吃。桑树不高,纸条不甚硬,可以弯折下来。哪里的桑葚又大又甜,有熟悉的小子带路,一畦一畦吃下来,牙齿舌头都是黑的,再偷偷回到教室继续午睡,老师能看不出来?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桑树被挖了,说是退耕还林?种几根竹子,换点补贴,县城里的缫丝厂丝绸厂也倒闭了,四乡八野,难见到几棵桑树。这延续几千年的好产业,在这个小山村就这几十年的时间就式微了,想想都是可惜。只是时代变迁,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庄,年轻人留守的已经很少了,又能继续存在多久呢?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anshaa.com/csxgls/1013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医药传统文化国医大师如此说系列国医大师
- 下一篇文章: 先进典型谌宏远桑蚕产业引路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