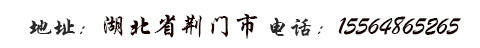叶天士为什么说病久入络
|
“病久入络”是叶天士医案中常用的一句话。照一般的说法,“络”浅而“经”深,怎么病久反而入络呢? 叶氏认为:疾病的初起,病邪多侵犯气分,经主气,所以说“初为气结,在经”;病进一步发展则侵犯到血分,络主血,所以说“久则血伤,入络”。关于先气病、后血病的说法来源于《难经》,叶氏把它结合到经络、营卫,作为辨证施治的基本理论,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发挥。 《内经》论疾病的浅深,分“孙络”、“大络”、“经脉”……逐步深入。叶氏所说的“病久入络”,意义有所不同。关于络脉的概念,早在清初医家喻嘉言写过一篇《络脉论》,他说十二经生十二络,逐级又分出“系络”、“缠络”、“孙络”,愈分愈小。稍大的在俞穴肌肉间,营气所主;小的分布到皮肤,卫气所主(见《医门法律》)。这里也是说的络浅,经深。那深部是否也有络呢?络脉既然是愈分愈小,漫布全身,体表有,内脏也有;浅部有,深部也有。叶氏所说的络,似应从这一意义来理解。 《内经》说过:“阳络伤则血外溢,血外溢则衄血;阴络伤则血内溢,血内溢则后血(便血);肠胃之络伤,则血溢于肠外…”这一论述给叶氏以很大启发,在医案中多处加以引用,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结合辨证,将络脉的概念更具体化了。他认为“经几年宿病,病必在络”。但病在哪一部分的络,则还要根据病情作出具体分析。如叶氏论中风为“内风袭络”;伏暑为“暑风久入营络”;瘕、疟母为“正虚邪留,混人血络”;脓疡为“瘀热入络”。他还细分“脏络”和“腑络”。如胁痛,有由于“肝络凝瘀”;大痛、大吐,或为“悬饮流入胃络”;“痛而纳食稍安,病在脾络”;经疏肺降气不效者,为“病在肾络”等。叶氏讲了这许多“络”,是否真像徐灵胎所评的“专以络字欺”人呢?似不能这样简单看。叶氏以“络”来辨证,同时也是以“络”来施治。例如对“中风”一证,以往常认为,风从外来,因而多用祛风一类药。叶氏创立了“内风袭络”说,用滋液熄风、濡养营络等法取效,就改变了这一情况,在中风辨证施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。对温热病,叶氏提出“吸入温邪,鼻通肺络,逆传心包络中……”的说法,这是《温热论》中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传心包”的张本。叶氏在张仲景用鳖甲煎丸治瘕、疟母的基础上,发挥了治络法,攻积除坚,多采用虫类药,说“通络方法,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”。又从旋覆花汤变化出“辛香入络”、“辛润通络”等法,以治痛证等。这说明,叶氏的“络病”说,在理论上和临床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。 叶氏还很重视奇经八脉理论的运用。认为奇经与络的关系密切。“通络兼入奇经”,两者有它的一致性。通络怎么兼入奇经呢?这里有个对奇经八脉的理解问题。督、任、冲、带、阴维、阳维、阴跷、阳跷这八脉,在《难经》中首次作了综合论述,说它们调节十二经脉的气血,有如湖泊之与河流。奇经联络各经脉,可说兼有络的特点。阴维、阳维,联合阴经或阳经,《难经》所谓“维络于身”。阴跷、阳跷,是从足少阴、足太阳分出,本身就可称作络。叶案中就有这样运用的例子。如说:“右后胁痛连腰胯,发必恶寒逆冷……乃脉络之痹证,从阳维、阴维论病”(处方:鹿角霜、小茴香、当归、川桂枝、沙苑蒺藜、茯苓)。又:“面赤痰多,大便不爽,此劳努伤肝,令阳气不交于阴,阳维、阳跷二脉无血营养……”(处方:金斛、晚蚕沙、汉防己、*柏、半夏、萆蘚、大槟榔汁)。前一例,后胁及腰胯痛兼恶寒,故从阳维论病,用药以温阳为主;后一例,为阳浮不交于阴,故从阳维、阳跷论病,用药以养阴为主。前方,鹿角能温阳、活血、化瘀,可认作是“通络兼入奇经”的代表性药物;小茴香、当归、桂枝、沙苑蒺藜,均是叶氏作为通络的常用药。后方,蚕沙、萆解则祛风湿以通络。维脉、跷脉均行于下肢,故肢体病痛常从两脉论治。 由此可见,叶氏所说“病久入络”和“通络兼入奇经”之“络”,不是指外部的浮络,而是指内部的络,是关于脏腑经脉的深层概念。 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anshaa.com/cspzff/300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苏叶*连汤加减治疗慢性肾衰25例
- 下一篇文章: 宝宝枕头如何选择,这个可是很有讲究,正